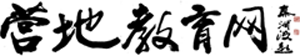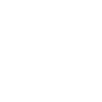贾平凹谈文学翻译
得知贾平凹先生的短篇小说《倒流河》荣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并且他本人将从陕西专程前来天津领奖的消息,我在第一时间给他发去短信,询问能否借助来天津领奖之际,与他见上一面?我知道贾平凹先生平时文学活动繁忙,加之个人创作时间宝贵,即便是来领奖,肯定也是来去匆匆,不会有太多的空闲接待客人。
出乎我的意料,贾平凹先生不仅很快回复了短信,而且答应可以在天津见面。他向我告知了航班时间,让我在他来津的当天晚上7点钟,在宾馆大堂等他。说来有趣,我和贾平凹先生建立起联系,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缘由是我们共同关注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工作:贾平凹先生是著名作家,而我是学习英语出身,这几年来,我们一直通过短信交流、沟通。这次如果能有机会与贾平凹先生当面交谈,于我来说将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盛夏的天津,云淡风轻,绿荫与繁花处处。6月26日晚7点,我准时在宾馆大堂等候贾平凹先生;将近7点半,贾平凹在接待者的簇拥下进入宾馆,我立刻迎上前去与他握手寒暄,并报上姓名。在办好入住手续后,我和贾平凹先生一起来到房间。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由于之前已有多年联系,此时相见全无陌生感。
早在2013年,为纪念孙犁先生诞辰100周年,《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策划了多期纪念专版,我代表编辑部向贾平凹先生约稿,他欣然应允,三天内便完成了饱含深情的《我见到的孙犁》一文,表达了他对孙犁先生人品与文品的崇高礼赞。又如,2014年3月,我加入中国翻译协会后,给亲朋好友发短信告知,没想到第一个回复信息的竟是贾平凹先生,他向我表示祝贺。我之所以向贾平凹先生汇报,是因为我在申报期间,曾跟他提及此事,他对我提出的“中西比较翻译”话题很感兴趣,他这样快地回复短信,足见对翻译工作的重视。中国翻译协会这些年致力于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2013年,中国翻译协会曾举办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面向海内外征集优秀翻译作品,题目中就有贾平凹的获奖作品《倒流河》。当时,我还请他关注大赛中涌现出的优秀译作。
在房间稍事休息后,我首先向贾平凹先生多年来对《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他今后继续为我们写稿。贾平凹先生笑着表示,有了作品一定会寄给你们。他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天津,三十年前,他曾专程来到天津看望尊敬的孙犁先生,那次见面,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随后,我们便将话题转向了翻译方面。我知道,贾平凹先生非常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也一直致力于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工作。而我则出于英语专业出身的本能、兴趣与爱好,近些年也始终关注着我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并与他们保持着联系,探讨相关的专业问题。比如,如何建立完善的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如何提高中文小说英译本完整度等等。
于是,我与贾平凹先生的对话,就围绕着我所钻研的“中西比较翻译”而展开。我希望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多听听贾平凹先生的观点和想法。
贾平凹先生仍然比较关心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工作,他向我提问:都说在文学翻译中,英译汉工作相对容易,而汉译英工作量更大,也更困难,是这样的吗?
我根据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原院长刘士聪教授的观点回答说:文学翻译远非应用文翻译,文学作品是用一种语言创造出来的具有独特意蕴的艺术。因此,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要传递原作中的艺术意境和字里行间蕴含的精神旨归。所以,为了使翻译作品能够最大限度地被一国读者所接受,应该由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进行文学翻译,即英译汉的工作应当由中国人完成,而汉译英的工作则应由外国译者承担。可惜的是,属于表意文字的汉字对于外国人来说太过复杂,他们不能系统而深入地认识汉字、领会字面背后蕴藏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因此,汉译英的高深工作于外国译者而言更是难上加上。
之前,我和贾平凹先生曾就这个问题做过交流。我说,可以通过中外翻译家进行合作的模式解决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难题。在这种跨国合作中,我们需要中方译者拥有更高的素质。这里的素质不仅仅是指翻译过程中的技巧与方法,更是要求中方译者对中文作品的全面深入的理解:因为中方译者需要向外国译者说明文本中所蕴含的多层次的思想内涵。翻译世界中并不缺乏完美的中外合作模式,例如: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沙博理(Sidney Shapiro)和凤子、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林丽君等,都是极具默契与水平的跨国合作典范。我还曾以类似模式进行过尝试,合作翻译了滕云先生的《孙犁十四章》的目录,因为文学翻译的本身难度,我感觉到翻译过程充满艰辛。但是我确信,对于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外译者合作的模式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贾平凹先生听后点点头,又说:我自己的作品翻译出去一些,影响不是很大,我看西方人未必喜欢中国作品。这就更需要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以更好、更准确、更丰满的翻译文本呈现在外国读者面前。
我读过贾平凹先生的一些作品,理解他这番话的深意,便将英美文学权威、南开大学原外文系主任常耀信教授的见解,作为回答:西方的意识世界建立在“原罪”的基础之上,当然文学与文化也不能避免。其文学文化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虽然有许多蕴含美好道德水准的作品不断面世,但到了当代,西方文学发展中出现了向负面、消极方向倾斜的作品。仿佛是一种“此消彼长”,物质生活愈优厚,精神愈加贫乏。而我国的文学传统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之上,文学创作多是劝人向上、向善、向往光明。
正是因为中西方在价值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西方舆论对我们的价值观并不能完全认同。但是世界文化应当“求同存异”而决不能完全同化。因此,面对西方世界对于我们文化、意识的不理解与不认同,我们要始终认清并保持自身优势,不迷茫亦不自傲,这样才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保持本质、特色与优势。
贾平凹先生曾就“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值得被翻译?”发表见解,认为翻译家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传递者,而如何选择有价值的作品进行翻译与传播更是至关重要。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记下孙犁先生的一段话:“中国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所选的是各国的进步文化成果,并不去找人家的落后或阴暗面也。但国外有些出版商或读者,对中国有这种想法,是很有可能的。从他们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著名翻译家葛浩文也曾遗憾地表示,他所翻译的作品对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是没有助益的。当然,我们更不能为了作品能被翻译到外国、被外国读者接受而创作。孙犁先生说:“我们不能提倡媚外文学。在三十年代,鲁迅把那种讨好外国人,以洋人的爱好为创作标准的文学,称作‘西崽像’的文学。”
可以说,通过高水平的翻译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仍在努力。我国的文学组织机构也在积极搭建平台,向外推介中国作家和作品。2013年10月,贾平凹先生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带去了中文版《废都》、《带灯》等作品。2014年8月,相关部门组织了由16个国家的30位汉学家参加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贾平凹先生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最终,与会嘉宾形成共识:文学最终还应该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而中华文明将以“明灯”般的精神文明形态照亮人性之美。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类文明更趋完善,更趋近“文明”一词的古义——富文采而光明。
我和贾平凹先生的这次见面,谈到的其实是一个很深奥的文学话题,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谈话激励着我继续学习与进步。从请我进屋到送我出门,贾平凹先生像老熟人般地热络亲切。我认为,我们之间的这种缘分与了解,不仅源自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建树以及对孙犁先生的景仰,更源于他自觉肩负的文化责任与担当。